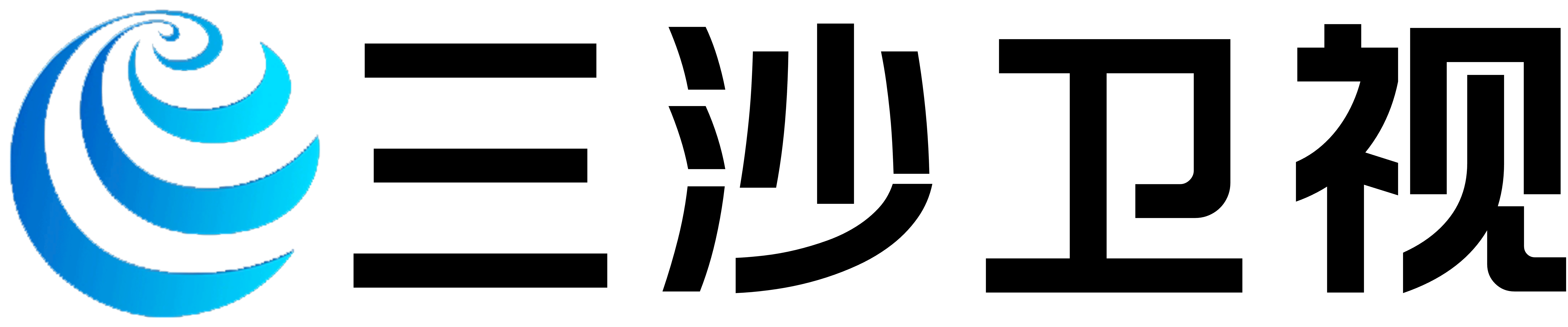
 下载手机客户端
下载手机客户端

他们是一群成天与数据打交道的人,他们以仪器为笔,在万里海疆丈量深浅、标定坐标。
他们是一群在数字经纬间锚定使命的人,他们用数据将海浪的瞬息变化、岛礁的细微地貌变得精准可依。
他们是一群海测兵。他们用这些带着海风气息的数据,为船舶提供“安全指南”、为海防打造“数字基石”。他们很少见到深海大洋的波澜壮阔,却在数据洪流中,托举着大国舰艇的每一次远征。
当潮汐起落改变着海岸线,这群坚守在舰船与岛礁之间的官兵,让数据有了穿透风浪的力量。今天,让我们走近海军某测量中队官兵,品读他们独特的“数据观”。
“陌生地域我们先走过一遍,后面走的人才能多一份心安”
清晨,海军某测量中队官兵起了个大早——测量某个小岛的岸线滩涂,以及附近海面上的明礁。为了这片测区,大家已经忙碌了数月之久。眼下,正是此次任务的“收官之战”。
乘小艇出发,有人负责开船、有人时刻观察情况。二级上士刘帅吹着海风,早已习惯了其中的腥咸气息,他用“浪迹天涯”形容自己的工作:“迎着风、伴着浪,在海天之间忙碌一整天。”
“浪迹天涯”并不容易。为了抵达最佳测绘点,海测兵必须爬过陡峭的岩石。海浪猛烈地冲刷着礁石,在凹凸不平的表面留下一汪汪水渍。上等兵闫子坤率先踩在礁石上,却没有站稳、打了个趔趄,所幸被身后的刘帅托住。
为了寻找最佳测量点,刘帅背过身,用脚一点一点试探落点;闫子坤伸出头去,时刻观察礁石情况,辅助刘帅找准位置。不知过了多久,几人才挪到了相对平坦的地方。
“每一次执行外业测绘任务,都会面临陌生环境的考验。”刘帅说,时间久了,每一个海测兵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疤划痕。这是海测兵的“徽章”,因为高程、水深这些专业数据,只能在最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寻找答案。
架好标尺、打开设备、信号回传、检查数据,一系列动作时间不长,海测兵们操作起来行云流水。重复了几次这样的流程后,脚底这块礁石的数据便被完整呈现在海测兵面前。
一天的任务远未结束,一行人又乘着小艇来到附近的海岛继续测量。扛着沉重的测量设备踩在松软滩涂上,每一步都走得艰难。意外落水、身陷泥潭,对于刘帅来说是家常便饭。
“滩涂周边的芦苇、杂草太密,要前后兼顾。”刘帅一边走一边叮嘱新兵,眼睛不离前行路线,时刻观察周边有没有暗坑、虫窝。
正值中午,战士们呼吸着沉闷咸湿的空气。不断滑落的汗珠,见证着他们的艰辛。相比于炎热,更漫长的,是远离人烟的孤独。
海上没有通信网络信号,海测兵只能借助电台与后方取得联系,随时汇报动向。渺渺海面上,一叶小舟缓缓向远方进发,面对广阔海天,刘帅这样的老兵,也难免生出孤寂之感。
勇敢者善于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中攫取幸福。一整天作业完毕后,看着夕阳一点点下沉,跃动的金光洒在海面上,在海风吹拂下战士们不禁感慨:“这一天,没白过!”
跋山涉水,追星逐月,海测兵已经习惯了默默行走在海岸线上。“世界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。”刘帅说,“陌生地域我们先走过一遍,后面走的人才能多一份心安。”
年年外出测海,每一处测区的特点各不相同。对于海测兵来说,只需要知道目的地在哪,然后迈出双腿、摆开双臂,勇往直前。
“任务再艰巨,把它除以一万,就觉得不再那么难”
在中队里,一级上士高铁车并不显眼。
高铁车在大学里学的是水深测量专业,专业和岗位的高度契合,让他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。但是时间久了,他也开始迷茫起来:“这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,到底有什么意思?”
在一次测绘任务中,为了一块面积10多平方公里的测区,战友们要搭乘小艇累计往返1000多公里。早起,测绘,晚归,整理数据,周而复始,平淡枯燥。
一天的工作量,在海图上看不出来。海测兵架设多少次标尺、身上多了几道划痕,只有自己知道,海图上并不会标注……
“我们也羡慕舰艇兵,操纵着威武的军舰驶向深蓝……”高铁车说。
但是测绘事业总要有人干下去,高铁车话里虽有羡慕,但是并无不甘。海测兵虽然没有壮阔航迹,但艰险任务努力完成后的那种满足感,与沿途欣赏到的壮美风景,交织成了他们的幸运与幸福。
祖国的海疆那样辽阔,想要为战舰更好地保驾护航,海测兵必须走得更稳一些,看得更细一些,尽可能把一处测区所需的数据都采集到。
在执行某次全数字地形测量任务时,中队为了准确测量岛礁的高度和面积,大家背着笨重的测量仪器在悬崖边缘行走,每隔10米就要测量一个高程点。他们在地形陡峭、杳无人烟的环境中,提心吊胆跋涉了整整一天,而这也不过是海测兵测绘工作中常见的一天。
1∶10000,这是海测兵最常用的比例尺,用来衡量、转换现实和地图的差距。
中尉王宝林对大家说:“你们看这个‘1’,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,只要日积月累,总有一天能达到后面的‘10000’;相反,没有这个‘1’,后面跟着再多的‘0’也没用。”
善用比例尺,这是海测兵的智慧:“任务再艰巨,把它除以一万,就觉得不再那么难;每当征服了1平方公里的测区,大家把心中的喜悦乘以一万,心头的干劲更足了。”
时光荏苒,今年是高铁车在中队的第14个年头,他早就抛去了刚入伍时的迷茫。坐在办公室,高铁车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点了一个点,笑着说:“这就是我一天的工作量。”
等无数个点连成一条线,无数条线汇聚成一个完整的平面,一幅海图就做好了。
“一是一,二是二,标注海图没有模棱两可一说”
仔细端详海测兵的脸庞,会发现这群年轻官兵面色黝黑。由于常年在野外风吹日晒,他们也变得像礁石一般粗粝而坚硬。
海测兵的生活确实粗糙:外出作业一整天,他们来不及制作可口饭菜,午饭晚饭经常吃着面包和单兵自热食品、就着矿泉水凑合一下;中午休息随便找个地方席地而坐,或者是在乘小艇途中趁机打个盹……
与之相对的,是他们在业务上的精细。执行外业测绘任务,测量设备就是海测兵的枪。不论是越险滩,还是爬峭壁,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设备,看护得很紧;等到测量结束,他们立刻把仪器收拢、及时保养,以防受到海风侵蚀。“测量仪被海风中的盐分侵蚀,就会影响测量精度,返厂维修也会耽误测绘进度。”官兵们道出了这份细致背后的原因。
一天,测量中队在海岸边搭设了验潮站,全天候记录潮汐的变化情况。二级上士王智超俯身读取水尺上的数字,经过一系列数学计算,得到潮汐变化的数据,为下一步测量真实水深做好准备。
晚上回来吃过饭后,王智超立刻坐在电脑前整理数据。他指着屏幕上蜿蜒曲折的等深线介绍:“我们获得的数据并不是直接使用的,还需要通过专业软件进行数据处理。”
夏日炎热,王智超无心关注脸颊滑落的汗珠,轻触鼠标剔除了影响真实水深的因素,把准确信息标注在海图上。他点开了最近几天正在处理的海图,上面绝大部分被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数据信息,王智超的视线聚焦在海图的空白部分:“这些位置都得认真标注清楚,一点也马虎不得。”
在二级上士于洋振眼中,大海就是由一组组数据编织而成的,温度、盐度、深度、磁力,这些数据标定领海基点坐标,为战舰远航点亮灯塔。看着一幅幅海图上的数据,虽然没有碧海蓝天的自然风光,却也给人一种“精确的美感”。
刚来海测中队的时候,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流程,于洋振一有空就查阅相关资料,背记测绘专业的知识,向老兵请教野外作业的经验。中队长王新成看着他努力的样子暗自点头:“是个当海测兵的苗子!”
测量数据再精准一些,标注海图再准确一点,这是于洋振和所有战友的期待。在一次测绘过程中,一行人踩着湿滑的礁石架设好仪器,获得了数据,却在最后标注海图的时候犯了难:这是一块经过海水侵蚀的礁石,长年累月的海水冲刷让它变成了上粗下细的模样,这类不规则礁石的标注难度很大。
有人提出只标注礁石上半部分的数据即可:“这么做不会影响礁石的位置信息,也不耽误海图正常使用。”于洋振较了真:“一是一,二是二,标注海图没有模棱两可一说!”他立刻查阅相关资料,想从专业书籍中找到这类不规则礁石的标注方法。凭着这股执拗劲头,于洋振最终把礁石的准确信息完整标注在海图上。
“管它有多苦,想想出海的大航母;不管有多累,海测的数据必须对!”这句顺口溜,是海测兵们工作生活甚至是性格态度的写照。让每一组数据都传递准确信息,发挥出战斗力,这是他们心中恪守的原则。
一丝误差可能让万吨战舰搁浅于暗礁,一串错位的数字能令潜艇驶向未知的深渊。当现代战争朝着智能化方向演变时,海图数据的精准绝非纸上谈兵的技术指标,它既是保存实力的底线,更是制胜的先机。在舰炮轰鸣的表象下,决定胜负的或许是一群海测兵笔尖下毫厘不差的等深线。
中队长王新成说,现在已经列装不少先进的测量设备,测量效率大大提高,但为了获得精准数据,海测兵的优良传统不能丢,还得练就“铁脚板”,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祖国的万里海疆。
清晨,海测兵依旧步履不停前往测区,小艇划过海面,留下一道笔直航迹。就像他们在海图上勾勒出的经纬线一样,简洁而有力。(毕笑天、付康)
战位观
测海先定心
刚来测量中队的第一天,班长把我带到学习室,桌子上摆着厚厚一本《海洋地形学》。翻开书页,那些复杂的公式与陌生的术语像海浪一样扑面而来,让人有些透不过气。
“我们的工作不是看出来的,是测出来的。”班长的声音很沉,手用力拍了拍书的封面。
那几个月里,我把自己埋进了理论学习里。潮汐计算、声呐原理、地质采样,每一页都必须完全理解。可真正难的不是死记硬背,而是如何在实际测量中应用——测绘不是纸上谈兵,一个疏忽就可能让几小时的努力作废。
第一次拿测量仪时,班长的表情比平时更严肃。那是一台锃亮的测量仪,外壳白得晃眼。他让我小心调试每一个按键,手指必须稳,操作必须精确。他说:“出了错,丢的是整个测区的精度。”
第一次出海那天风浪很大,船摇得厉害,我却只顾着紧抱仪器,生怕磕碰到。测量点选在一座远礁上,礁石长满青苔,踩上去又湿又滑。我按步骤开机、调试、采集数据,屏幕上的曲线一点点连成完整的图形——这是海测兵特有的成就感,仿佛大海正在你手中被揭开神秘面纱。
可刚测到一半,仪器突然报警,屏幕闪烁异常信号。我一下子慌了,反复检查连接线、重启设备,却还是无法排除故障。海风吹得指尖发麻,后背却渗出汗来。
看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,班长指了指不远处的信号塔,示意我转移到开阔地带再试试。他看着我重新校准设备,只留下一句话:“测海先定心。慌,是最大的干扰源。”
那天回程的船上,班长和我多聊了几句。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岛说:“以前,我们还用老式经纬仪和水准仪测量,一个岛要四五天。现在有了新装备,一天就能完成。”
后来,我也经历了很多次测量。从海岛到滩涂,从风平浪静到惊涛骇浪。有时候船摇晃得像要把人甩进海里,有时候信号始终不稳,有时候仪器突然“罢工”。可渐渐地,我不再慌了,因为我知道——不管数据多难测,终归是能测出来的。
再后来,又有新兵和我一起出海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仪器,像捧着宝贝一样,而我站在一旁,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模样。海测兵的路,从来就不是平坦的,但每测完一个点,海图的空白便少了一块。
来源/新华社
监制/黄丹 叶微
主编/汪进威 王欣
编辑/丁灿
@三沙卫视
